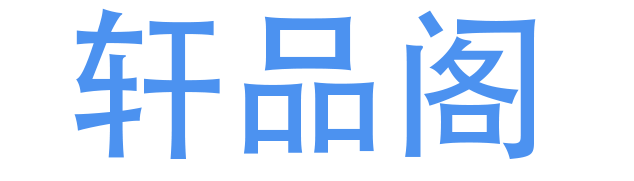全世界有810万人在等着接听一通陌生人的电话。
“我其实非常讨厌打电话。”24岁的留学生胡卓依说。舞台剧演员何滟滟不喜欢与陌生人交流。生于东北的张卢害怕寒暄。大学生崔桐芮说自己是“i人”。但目前他们都是这810万人中的一个。
这超出了Be My Eyes开创者汉斯·约根·维伯格的想象——有人会把一个从未用过的App保留几年就为了接到一通陌生人的电话。
2012年当他在丹麦萌生出创造一个不收费的应用软件让明眼人通过视频通话帮助视障人士的想法时他能想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找到志愿者。
现在Be My Eyes上注册志愿者的数目已经超出盲人的10倍有余他们来自150多个国家组成了这个“全球最大的数字视障志愿者组织”。志愿者们热切地期待能接到一通“辨认袜子颜色”“看看红绿灯”之类的视障求助电话。他们说自己在日常也会帮助其他人但没如此开心。网络使大家变得更热心了吗
一位志愿者说:“这个软件打动我的不是技术或界面而是它唤起了我帮助其他人的冲动和幸福感。”
等待看见
只不过电话很长时间都没打来。
中国是全球视障人数最多的国家。截至2023年国内有超越1700万视力障碍人士占全球视障人口约18%。
而在全世界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的数据显示约有12亿人患有某种视觉障碍其中至少4300万是盲人至少2.38亿人是低视力。
可是他们到底在哪儿
Be My Eyes上只有72万盲人注册。“当你看看世界上盲人的总人数时你会发现大家基本上什么都没做。”开创者汉斯·约根·维伯格 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真的期望大家能在将来几年里扩大规模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速度非常快。”
这是一个巧妙的通道。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2023年统计显示全球54%的人口拥有智能手机。假如其中有人想做点好事他们不再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去一个特定的地方仅需在空闲时拿起手机睁开双眼。“就算我在工作我也可以提供一会儿帮助。”志愿者黄秀峰说。
只不过志愿者们心知肚明接到电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国内持证的视力残疾人中44%在60岁以上他们多数受教育程度低不擅长用手机。一位网友给盲人爸爸下载了Be My Eyes“但他一直不好意思麻烦其他人也一直感觉我忙不想麻烦我”。24岁的盲人李春隆说他身边用这个App的盲人不到一半他猜测“这上面还是外国人居多”。
大家能从Be My Eyes的主页上看到实时增长的盲人和志愿者数目——72万∶810万一个悬殊的比率。
同时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一些研究发现互联网中助人者越多利他行为越容易发生。统计学改变了施助者的心理使做好事成了和中彩票一样的概率事件两者都值得开心也值得等待。
张砚斐2019年就下载了Be My Eyes成为志愿者在这之后的4年一通电话也没接到。其间她换过三四次手机这个蓝色图标一直留在屏幕主页。
曾有志愿者说:“这个应用让我感觉自己非常有用我仅需掌握怎么样迅速拿起我的手机。”但事实上抢到电话并困难。这类年张砚斐起码错过了五六通电话。每当铃声响起志愿者需要迅速反应按下接听键不然电话就会被其他志愿者接听。
这恰好构成了何滟滟下载是什么原因。由于排练和开演时手机不在身边担忧错过电话她一直没下载。直到获悉这通电话会同时转接给多人十月十日她才正式成为志愿者。
过了一天她就幸运地收到了求助来电。但她把手机平放在餐桌上纠结起来。
在以往的日常施助者一直在有所筹备的状况下帮助其他人。大家一直在熟知了场景、对象之后再决定是不是要向前一步。但在这里接听之前所有都是未知。
看到来电的几秒钟内志愿者会历程开心、紧张、焦虑、犹豫等种种情绪。“担忧自己抢不上又怕自己抢上了。”何滟滟说。
十八岁的志愿者赵小祺说她常想在现实日常帮助其他人但父亲总让她保护好自己。互联网的场景隔离给人一种安全感利他的冲动可以超越恐惧与不安。
何滟滟按下了接听键。
被选中的人
两个世界联通的那一刻氛围有的紧张。双方都携带陌生的试探用何滟滟的话说:“仿佛我害怕他诈骗他也害怕我诈骗。”
一个男声问:“用你们这个软件能提供什么帮助能帮大家不少东西吗”何滟滟意识到他们都是首次用他把她当成了员工。
依据后置摄像头的画面何滟滟描述了他身边的环境和物件。在听到回话后他们听起来放心了一些。“他感觉挺神奇的还挺快乐的。”她说。
他问我们的工作服是不是干净有没脏污。摄像头转到左肩又转到右肩何滟滟发现他是一个胖乎乎的男孩看起来30岁左右。白衣服左胸处有“盲人技师”一类的字眼。她告诉他们衣服非常干净。
他们好像是在宿舍身边还有其他盲人。他们一边询问一边讨论。面对这么多陌生男士何滟滟也有的不安。
几个问题之后电话结束得很出人意料。何滟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误触了。“也没说谢谢之类的一下子就结束了。”
她反复想是否自己不够热情打击了其他人求助的信心。
而志愿者曹振翔意识到自己太过热情。他担忧帮不到他们紧张得手抖还要努力平复语气防止吓到他们。帮一位大叔确认面包的保质期后双方剩下的时间“大多数都在讲谢谢”。“人家说谢谢我也在说谢谢我也不了解我在谢什么。”曹振翔说。
生疏一直在所难免。崔桐芮从来没在日常见过盲人。十月1日她跟朋友在电影院候场时接到了求助电话——一位盲人女性需要找到掉在地上的钥匙。 三洋全自动洗衣机拆装视频教程
镜头绕了几圈除去白色的瓷砖和一只狗爪她什么也没看到。两三分钟过后她愈加着急情急之下问:“钥匙是哪种颜色的”他们说不了解。
崔桐芮意识到刚刚的问话可能有的冒犯她沉默了一阵说了一句对不起。十几秒之后电话中断了。
进入影厅的前十几分钟崔桐芮什么也没看进来。她深深自责:“半夜躺在床上都想坐起来质问自己我如何如此呢”
她觉得自己应该学习怎么样在言语上帮助视障人士。“想象自己是一个看不见的人我会想要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帮忙。”譬如精确地描述防止语序混乱和模糊。
武秋怡把当志愿者的历程推荐在社交媒体上时补充了一句:“期望大伙多一些耐心视障人士的语气或者语序或许会和大家有的不同。”她曾参加过残障人士的公益活动知道他们的社会化程度:“能在App上求助的大多是会用手机、有工作的视障朋友还有不少人是不太外出的他们也看不到大家说话的反应所以语气或许会有一些生硬。”
事实上Be My Eyes的用户极少在电话里聊天。他们的对话常以“你好我想……”开头以“谢谢再见”结尾。据开创者介绍这里90%的通话时间不到两分钟。
这正是这个App受青睐是什么原因:它知道视障人群的心理——他们正是为了避开情感联系而来的。日常他们有太多需需要助的时刻但无论对亲友还是身边的陌生人他们一直不确定他们是真的便捷帮助他还是出于礼貌不能不帮助他。
而志愿者是经过选择来到这里的。视障人士不必在乎眼光、人情或负担。假如志愿者不便捷接听电话会继续转接。“在这里视障人群可以请求帮助——但不需要真的请求。”开创者 汉斯·约根·维伯格说。
考虑到视障人群的心理张砚斐说她一般不会想要在电话中聊更多。她换位考虑:“是否会增加他们的愧疚感假如我是寻求帮助的人我期望尽快解决问题尽可能不浪费志愿者的时间。”
为了在深圳的机场找厕所盲人李春隆发出过一次求助。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孩她非常难通过狭小的手机屏幕找到指示牌当看到一个路人出目前镜头里她索性冲着他们喊:“你好他双眼不好能否带他去厕所”问题就如此解决了。
李春隆感觉这个女孩非常知道视障群体。“不少盲人自卑非常难主动去跟身边的人交流。”他说“从小遭到的语言攻击太多了。”他曾在一次问路中被路人反问:你一个瞎子出来做什么
接过一通电话后曹振翔自如了很多。9月12日他一边打着电脑游戏一边帮一位盲人过了马路。日光晃眼曹振翔看不清远处的红绿灯只能指示他们拿着手机转一圈正好看到旁边有一些人也在等红灯。他请他们稍等自己又打了会儿游戏直至镜头里的人群开始移动。“可以走了。”他说。“很平时就像是跟朋友打电话帮他找了个东西一样。”
迈出一步就多了一些自信——电话两端的人都是这样。由于一些微小的勇气与善意两个世界的大门就如此缓缓被推开。
迷茫的生活中一件确定的好事 下水道反味特别严重怎么办
愈加多明眼人“看见”了那个遥远的盲人世界尽管视线一直模糊的——很多盲人都有摸手机摄像头的习惯那是手机上唯一凸起的部件只不过常常摸就会脏。
“你得提醒他们擦。”24岁的李春隆说。他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加视神经萎缩“是特别全的盲一点光感都没。”他说话间常开玩笑携带一股年轻的乐观与希冀。“我相信世界上是有光的。”他说。 led维修费
Be My Eyes开发了如此一个功能志愿者可以远程打开盲人手机里的闪光灯。有位志愿者在晚上接到视频通话屏幕一片漆黑有人在黑暗里问:我的电饭煲是不是开着那位志愿者才意识到他们是无需开灯做事的。
为了帮一位大叔检查房间的灯在摇晃的镜头里志愿者张卢看到了他的屋子。几乎没任何装饰卧室里没凳子也没床头柜甚至连床头也没只不过靠墙放着一块长方形的床垫上面铺了张素白色的床单。“刚开始有点惊讶感觉挺悲伤的但又感觉合乎常理他的房间应该是如此的尽可能降低障碍。”张卢说。
张砚斐在公司里帮一名盲人男孩查询面条的保质期时发现已经过期两天了。挂断电话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在颤抖。旁边的经理和同事知道出她的异样。“他的声音非常不错听中文也很规范给我的感觉本应该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人。”她有的哽咽“目前吃一包面都要其他人来帮忙”。
口罩的正反面、行李箱的滚轮密码、腊肉包装上的口味、操作洗衣机的按键……当看不见的困难嵌入生活的细枝末节明眼人才真的理解那个世界。开创者汉斯·约根·维伯格介绍Be My Eyes中的很多电话都与颜色、数字、温度有关“家的大部分机器都不合适盲人用”通话的场景多半是厨房或街道。
有志愿者帮一位盲人妈妈检查孩子的作业看田字格中的“下”字写得怎么样。一位盲人不小心把开水倒在了地上向志愿者确认是不是烫到了我们的狗。
也有的“看见”是出人预料的。志愿者胡卓依帮一位弱视阿姨挑选过旅游要穿的裙子。他们的需要是颜色鲜艳、拍照好看。胡卓依替她选了一件碎花的和一件绿色的。
是的视障群体也会旅游。他们通过气味、环境和四周的人声感受风景。这是李春隆的喜好他去年去了广州塔今年又在苏州的周庄古镇住了两天。他选了一个小桥流水的地方坐着听环境音和过路人的谈话。“他们或许会聊到这个景点每一个人说的都不同我就综合起来提取我们的理解。”
他还喜欢摄影——一个和他“没任何关系”的兴趣。他买了很多摄影设施包含运动相机、手持杆、支架……Be My Eyes中的人工智能识图功能能帮他读取视觉信息若是和铜像合影他会先摸一摸拍十几张角度不一样的照片然后让明眼人朋友挑出其中最好的一张。
“这也是我的回忆可以和朋友推荐作为我去过这个地方的一个凭证。”他说“等大家上了年龄也可以和后辈儿孙推荐大家年轻时候的故事。”
志愿者武秋怡在山东经营着一家奶茶店今年开始营业后不久妈妈过世了。23岁的她度过了一段虚无的时光。她感觉自己没办法成为有名的人、作出大贡献或者是“把世界变得和平”甚至“赚钱也没什么用”子欲养而亲不待了。
9月25日在奶茶店的吧台里武秋怡接到了自己在Be My Eyes的第一通求助电话帮一位盲人确认了火腿肠的保质期。她将这段历程发到社交媒体上有150万人点了赞。很多志愿者在评论区别享自己接听电话的历程。
武秋怡说网络带给她一种奇妙的感受就像走在路上和人擦肩而过他们看着非常平凡但也会在做对某一类人有要紧意义的事情——每个路人都可能是如此的。
她用好看的花朵装饰奶茶店来店里的人林林总总并不了解那些假花源于残障群体之手是武秋怡常去做志愿服务的残疾人学校寄来的。几年前她成为遗体和器官捐献志愿者。“我做这类事不是为了向世界表明我是一个多么高尚、多么乐于奉献的人而是我尊重每个生命。”武秋怡说。
目前她常常看着盲人博主的视频入睡。“他们的视频非常慢非常安静。”
“Be My Eyes并非在拯救其他人的生命但它确实改变了大家的生活。”开创者汉斯·约根·维伯格说“有时我甚至会怀疑自己帮助最多的人是哪个这真是太神奇了由于志愿者们也很开心。”如精神病学家卡尔·梅宁格所说爱能拯救人——不论是施与爱的人还是得到爱的人。
一位志愿者过去推荐道:“那天失眠心里非常乱非常空感觉自己找不到理由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下载了软件后心里忽然就安静下来了我了解孤独无能的我某一刻也能成为其他人的双眼。”
本网站的文章部分内容可能来源于网络和网友发布,仅供大家学习与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站长进行删除处理,不代表本网站立场,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https://www.xpgjjw.com/keji/8451.html